
重塑藏经洞:与谢晓泽的对话
谢晓泽是斯坦福大学(Stanford University)“保罗·L·沃蒂斯与菲利斯·沃蒂斯”(Paul L. & Phyllis Wattis)讲席教授。他的艺术创作涵盖绘画、装置、摄影及多媒体项目,探讨历史、记忆与知识的主题。在本次采访中,谢晓泽讨论了他围绕中国西北地区莫高窟藏经洞(第17窟)展开的跨学科艺术项目。藏经洞于1900年被发现,洞内封存着五万余件手稿、绘画及文献,年代跨越公元4至11世纪。这些珍贵文物随后被散布至全球各大机构,主要收藏于大英图书馆(British Library)和法国国家图书馆(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)。本次对话是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(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,University of Chicago)“流散海外中国艺术数字化工程”(Dispersed Chinese Art Digitization Project)的一部分。

赖青琳 (Ellen Larson):首先,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自己的专业背景,以及是什么契机让您投入到敦煌项目中?
谢晓泽:过去,我一直从事与图书馆藏书相关的创作——绘画、装置、影像艺术——同时也涉及书籍的毁坏与焚烧,图书馆的摧毁,以及审查制度的问题。我的创作始终关注历史、时间与记忆,以及历史记忆与知识的脆弱性。
我与敦煌主题的缘分始于2016年,当时我受邀参加由敦煌基金会(Dunhuang Foundation)组织的一个小型贵宾参访团,该团由倪密·盖茨(Mimi Gates)和露西·孙(Lucy Sun)牵头。尽管此前已通过照片见过壁画,但那是我第一次亲自前往敦煌。参访期间,他们正在讨论在莫高窟设立艺术家驻地项目。
次年,敦煌基金会邀请我成为该项目的首位驻地艺术家。我当时感受到一定的压力,因为敦煌具有极为独特的历史地位。张大千、常书鸿、段文杰等前辈已在此做出了大量卓越的工作,因此我必须尝试一些不同的、全新的路径。
2017年夏天驻地之前,我做了大量研究,阅读了许多相关文献,而我的思考总是不自觉地回到藏经洞。这座洞窟拥有极其复杂的历史,同时承载着庞杂而百科全书式的文化遗存。

赖青琳:您能描述一下驻地期间是如何展开这一项目的吗?
谢晓泽:2017年夏天,我在那里待了大约一个月。当时,敦煌研究院为我提供了一间非常理想的工作室,里面有长长的木墙,嵌有金属板,这样我可以用磁铁轻松固定大张纸张。我开始创作一幅卷轴绘画,采用八尺整纸(约2.5米长)的宣纸。
我逐段绘制水墨画,将笔记、引用、图像和图表结合在一起。在此基础上,我开始构思三维雕塑和装置作品。与此同时,这些绘画本身也可以作为独立的艺术作品。这便是整个项目的起点。

后来,我在画卷中扩展了主题,加入了中国古代天文和占星学的元素。我还研究了西域地区的灭绝语言,并将其中一些融入作品《文字之雨》(Rain of Languages)——一场文字的雨——不仅包含汉字,也包括已消逝的语言文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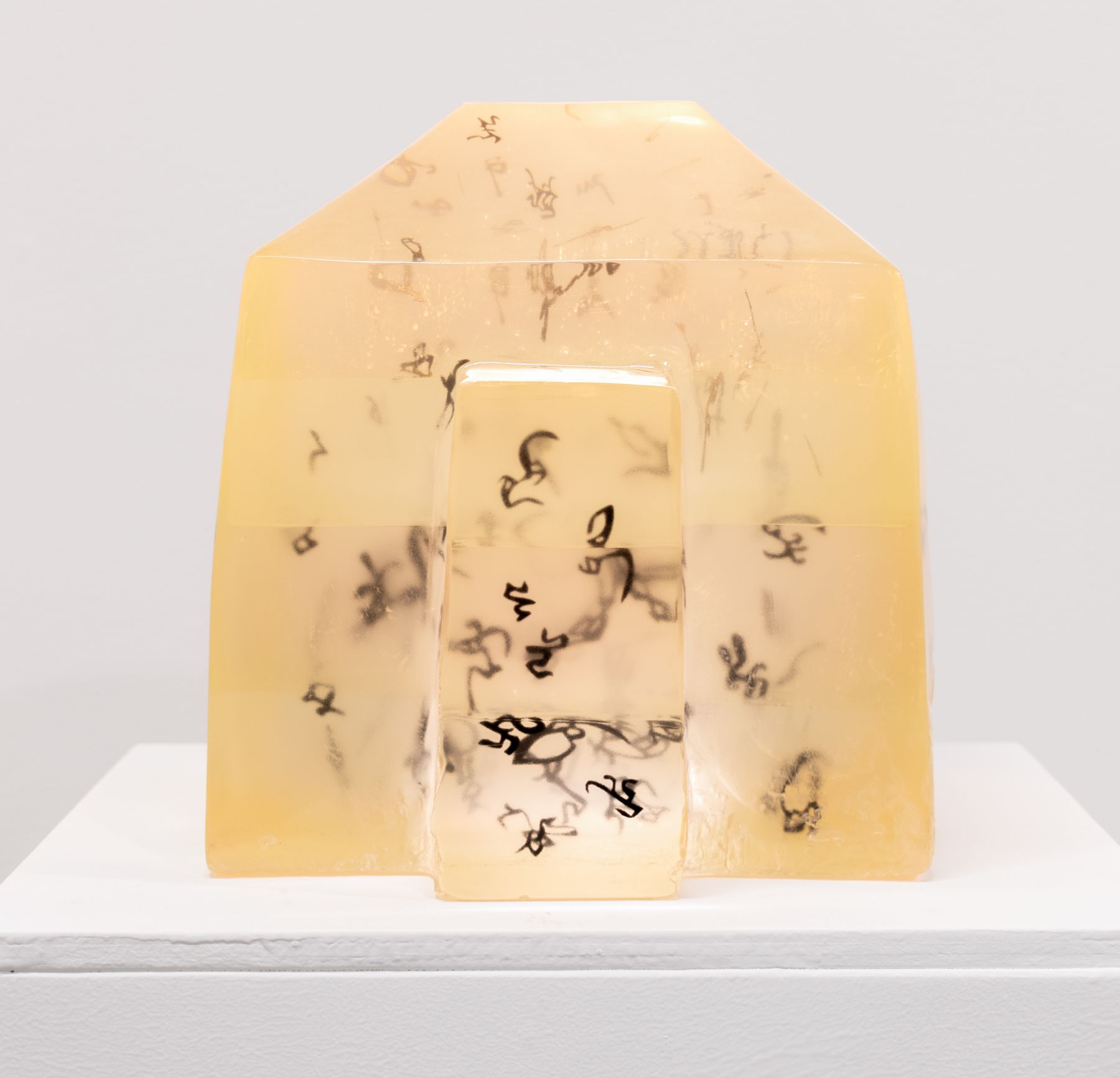
直到2019年,我才得以开始尝试雕塑创作。那年,我前往深圳,找到了一家树脂工厂,并开始进行一些实验。随后,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,项目一度被中断。但最终在2023年春天,我得以重返工作,并完成了一组三维作品。
最近,我创作了一件名为 《宇宙模型》(Models of the Universe)的三维投影作品。这是一种3D投影映射(3D projection mapping)——通过沉浸式投影在立体空间中呈现,灵感来源于藏经洞的内部结构。作品呈现出洞窟内部不断变化的景象,其中包含不同形式的佛教宇宙观,如 “三界九地”(Three realms and nine levels)以及各种曼荼罗的相互转化。这些模型从具象逐渐演变为抽象,最终变得纯粹几何化。
赖青琳: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一点是,您如何在不同媒介之间转换——从最初的二维绘画,到三维雕塑作品,再到如今的数字影像创作。
谢晓泽:我一直以来主要以绘画为主,但我曾在清华大学接受过五年的建筑学训练。这对这个项目影响很大,因为它涉及对内部空间及各种结构的想象。这些绘画结合了中国画的笔法——如传统山水、岩石、流水等元素——以及建筑语言。我小时候练过书法,虽然没有特别深入,但近年来,尤其是自2017年以来,我对书法越来越感兴趣,并认真投入其中。我觉得这个项目让我得以将自身不同的经验、知识与技艺融合在一起。
赖青琳:我认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,您的作品灵感来源于一个真实存在的空间,人们可以实际进入。但您的作品本身却创造了一种无法进入的体验,观众只能从外部观看。对此,您怎么看?
谢晓泽:是的,正是如此。这种“内部与外部”的关系——而外部的形式实际上是内部空间的翻模,是内部的投影。
深圳的展览有所不同。它没有3D投影,而是放大了藏经洞的空间结构。由于美术馆的空间尺度更大,这个作品转变为一种VR体验。观众需要排队佩戴VR头显,进入一个类似帐篷的结构,整个空间由厚实的手工纸包裹。我还与一群当地书法家合作,在这个空间中书写漂浮的文字,进一步构建出更大规模的“文字之雨”概念。


赖青琳:您之前也提到过自己的建筑背景。无论使用何种媒介,空间的表达以及观众与作品的互动是否始终是您考虑的核心?
谢晓泽:是的,我的建筑学背景,以及对空间与空间体验的兴趣,一直贯穿在整个项目的思考中。即便最初的作品是水墨画,它们其实也是关于空间的。在藏经洞项目中,我最初是将洞窟内部空间视为一个基本单元——一个不断上演各种戏剧的剧场空间。
格雷格·潘希拉(Greg Panciera):在这个项目的不同阶段和各种表达形式中,是否有一个核心概念让您不断回到它?
谢晓泽:最初,这个项目看起来有些零散。对洞窟中不同材质与物品肌理的研究,似乎与佛经文本的具体内容没有直接联系。但最终,它们开始相互关联。
当我研究洞窟中的各种曼荼罗时,我突然意识到,这些曼荼罗本质上也是世界模型。它们与“三界九地之图”画作中的宇宙观非常相似。
后来,我在大都会博物馆(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)的馆藏中发现了一幅元代的挂毯——《须弥山坛城》 (Cosmological Mandala with Mount Meru),它实际上就是曼荼罗与“三界九地”元素的结合。于是,这些看似分散的线索最终连成了一张更大的网络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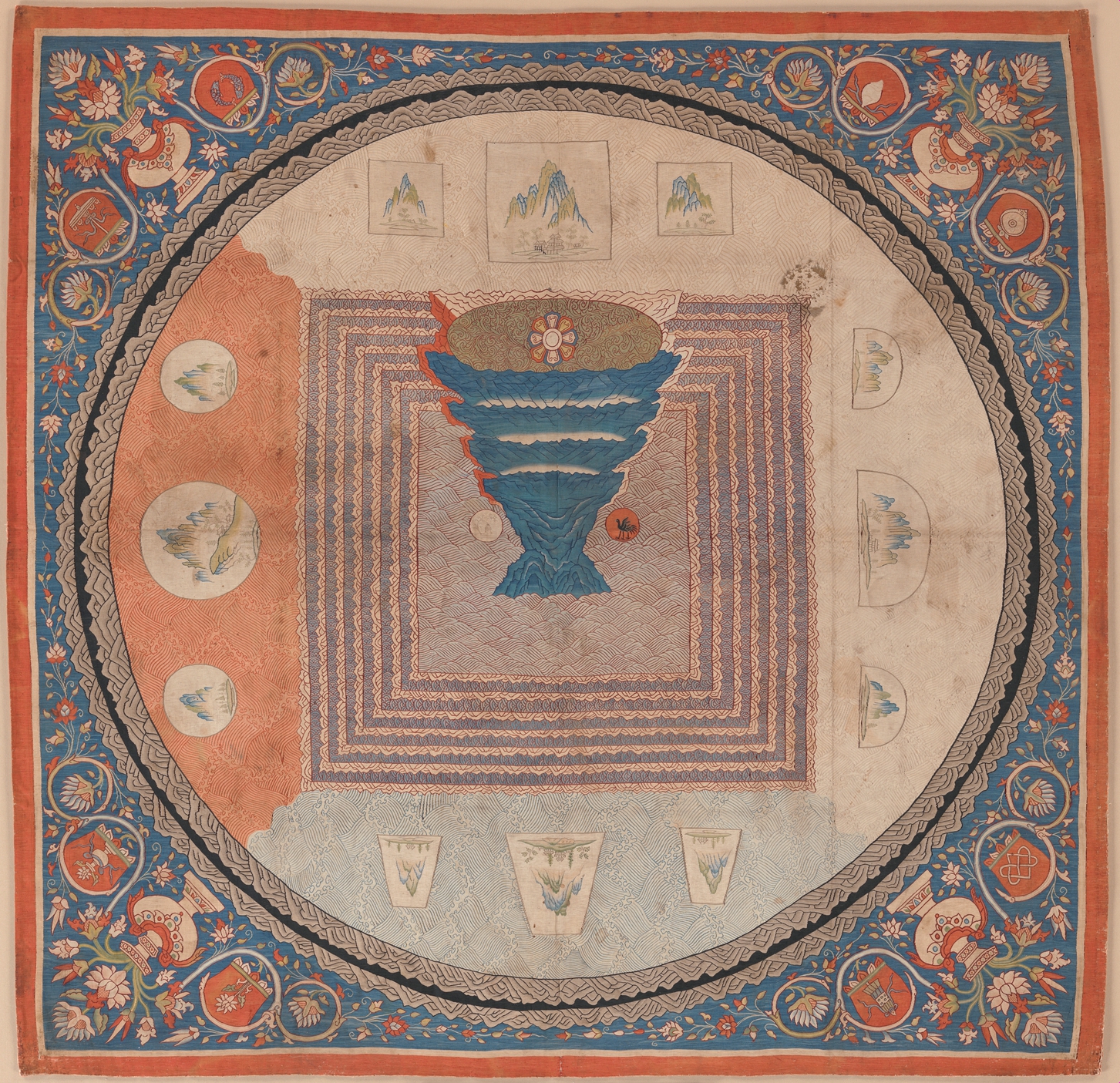
不同的曼荼罗总是与特定的佛经相联系——每一种形式都基于某一部特定的经典。它们之间存在相似之处,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,变得越来越精致和复杂。起初,我觉得这有些难以把握,但最终,所有线索开始汇聚。这一切都关乎“世界观”(world view)或“世界模型”(world model)。因此,“宇宙模型”(Models of the Universe)或“世界模型”(Models of the World)这一主题,实际上是在最后才逐渐浮现出来的,而整个项目的不同部分最终也都指向了这个方向。
赖青琳:在您的网站上,您将这个项目描述为“重塑敦煌藏经洞”(Reinventing the Library Cave at Dunhuang)。我很好奇,您为什么选择了“重塑”(reinventing)这个词,而不是“重建”(reconstructing)、“修复”(restoring)或“再连接”(reconnecting)?在这个项目中,“重塑”对您意味着什么?
谢晓泽:“重建”更侧重于对历史场景的想象——比如,1907年斯坦因(Aurel Stein)到来并带走文物之前,这个空间可能是什么样子?我们很清楚1908年在伯希和(Paul Pelliot)进入藏经洞时,它的大致状态。这些都是基于想象,而想象本身也包含某种程度的“重塑”。如果我只是想象和重建过去,我可能会称之为“再想象”(reimagining)或“重建”历史。
但“重塑”的部分——要让这个词真正发挥其分量——指的是后期创作的部分,比如,我自由地组合不同的曼荼罗,将它们转换为几何形式,并构建出这些相互交织的结构。在这一过程中,我开始感觉自己在突破传统,不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佛教图示或理论。这更像是:“基于这些已有的元素,我自己的宇宙模型会是什么样的?”
还有一个版本,是关于材料的分析——纸张、丝绸、麻布、木材等。这些材料仿佛在溶解后沉积成层,就像岩石的形成过程。这在现实中当然是不可行的,但它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——一种雕塑家、艺术家,甚至诗人可以探索的方式,而不是考古学家的研究方法。

我有一幅绘画,卷轴的第一部分,名为《浩繁经帙》——意为“浩瀚的卷帙”——它想象了卷轴是如何从后墙开始堆叠,随后延伸至两侧的墙面。这更接近于一种考古学意义上的重建,尝试推测历史上可能发生过的场景。因此,这部分作品更贴近学术研究。而在创作的另一端,则是更加自由和富有想象力的“艺术化”表达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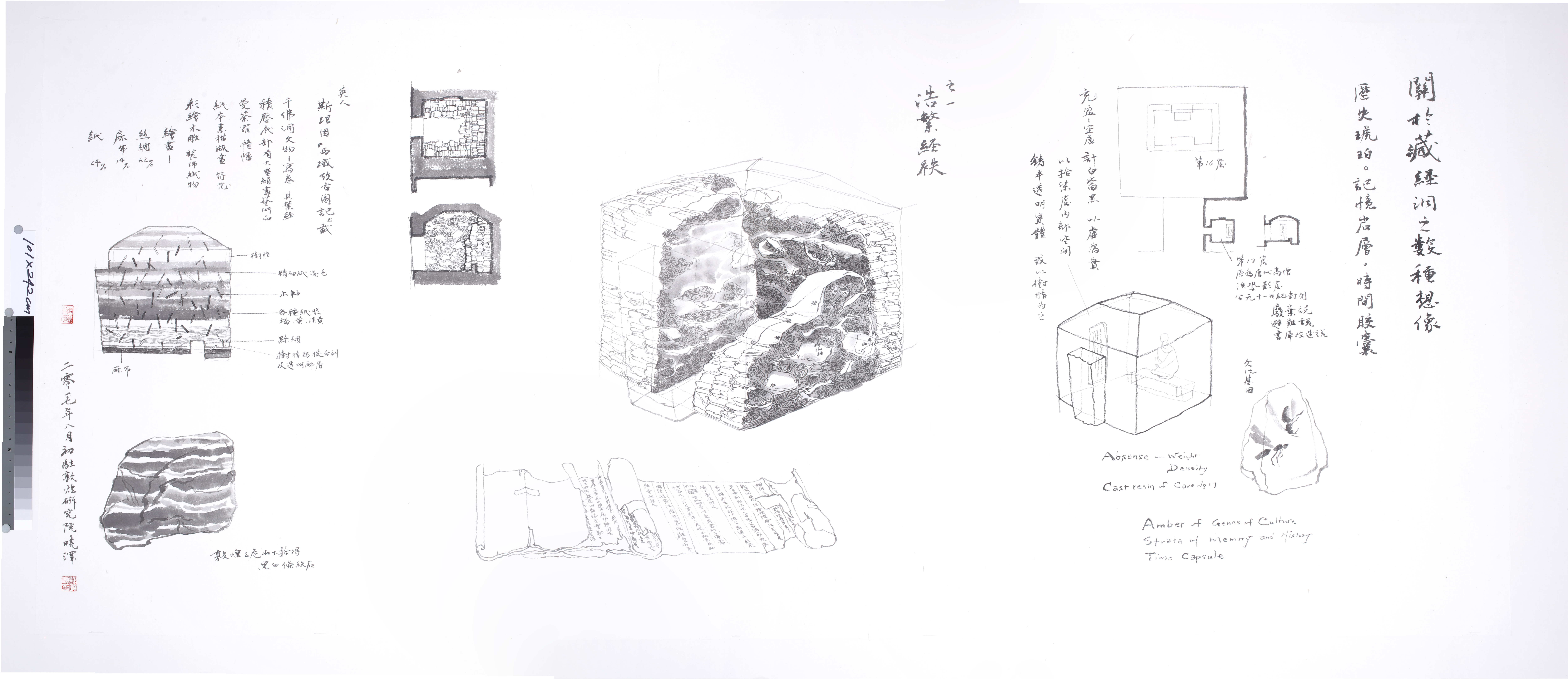
格雷格·潘希拉:在投入精力时,您是否会纠结于应该更倾向哪一方面?或者说,在这些不同的学科之间,您如何划分界限?
谢晓泽:这是个好问题。我对敦煌学——也就是关于敦煌的学术研究——其实还很陌生。我的借口一直是:我不是历史学家,也不是考古学家——我没有那个资格。但我是艺术家,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。没有绝对的对错,对吧?所以我感到非常自由。我可以天马行空——像天马一样在天空中翱翔——让各种想法自然浮现。
另一个让我感到自由的想法是:这不是一件完成的作品,而是一个持续进行的项目。它更像是笔记、速写,帮助我理解、构建事物。这个过程是完全开放的......当然会有错误——比如,一开始我的书法很生涩。那又怎样呢?但整个过程都保留下来了。卷轴上有日期,它是一种非常真实的记录。
所以,基于这两点,我觉得自己可以毫无顾虑地在不同的方法之间自由切换。很多时候,在讲座中我会自嘲,说自己是“业余考古学家”、“学者”,甚至是“伪考古学家”。有一次,我和巫鸿(Wu Hung)交谈时,他立刻指出:“你是一个当代艺术家!” 但我的想法是,把分析性的思维与创造性、想象力,甚至诗意的思考结合起来——对我来说,这是一条新的探索方向,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。
赖青琳:在类似的思维下,您在当代艺术家、考古学家,或者如您所说的“伪考古学家”之间不断转换。我还想了解您的亲身经历——您曾在敦煌,即藏经洞所在地驻留过,同时也去过大英图书馆,那里保存着大量敦煌文献。您第一次看到那些佛经时的感受是什么?您如何看待这些地点之间的分离?
谢晓泽:我在莫高窟驻留期间,住在莫高山庄。从我房间的窗户望出去,能看到北区的一排洞窟,那是当年僧人们居住的地方。而在左侧,便是藏经洞所在的区域。早晨,我有时会走出酒店大门,经过道士塔——王圆箓的墓地所在——然后进入那些洞窟所在的区域,其中就包括藏经洞。
在那里——而且大部分时间是独自一人——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。这种感觉仿佛与世隔绝,像是身处另一个时空,彷佛回到了1907至1908年的敦煌。那个时间点似乎近在眼前,仿佛斯坦因刚刚带走那些经卷,而王圆箓仍在人世。这种现场体验对我后来的创作,尤其是在作品中表达的诗意感受,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我将那种感受带回加州,在自己的工作室里继续创作。但那种亲历的经验、那种触动,是无可替代的。
在敦煌研究院的库房里,我曾亲眼见过一件北朝时期的卷轴——这是研究院馆藏中极少数真正来自藏经洞的文物之一。那是一部《大般涅槃经》,具体为《如来性品》,采用北朝时期的隶书书写。后来,在我的水墨绘画和雕塑作品中,我大量借鉴了这种书法风格。至于大英图书馆,其实我至今还没有亲眼看到太多来自藏经洞的原始文献。但本月底我将前往伦敦,届时就可以更深入地接触那些珍贵的藏品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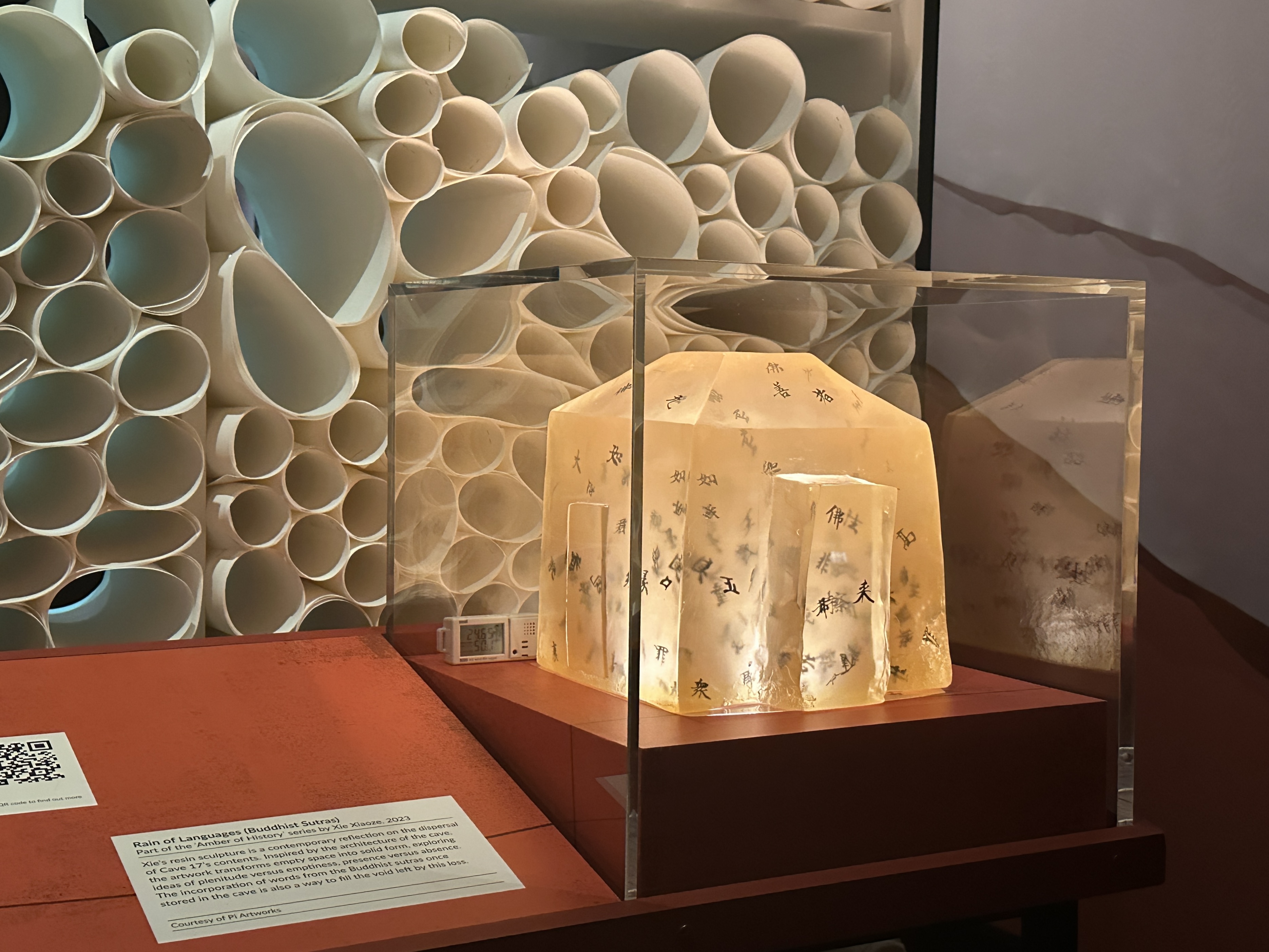
赖青琳:是什么促使您选择VR或数字投影作为创作工具,而不是继续在二维绘画或三维雕塑领域进行探索?
谢晓泽:从一开始,即使是在创作那些二维绘画时,我的思考方式始终是围绕三维空间展开的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,我一直希望能够实现一个《文字之雨》的简化版本——以三维投影的方式来呈现。后来机会出现了,我得以与更多合作伙伴一起工作,这才促成了这次3D投影的实现。
VR则是另一回事——最初我并没有考虑使用VR。在策划坪山美术馆的展览时,我原本打算制作3D投影,但由于资金限制,他们无法支持这个项目。后来,他们建议我参与一个现有的VR项目,并将我的作品作为其中的一部分。就这样,这个VR项目得以推进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与VR团队进行了几次会议,也学习了不少新知识。有些想法并不适合通过VR来呈现,他们也坦率地指出了问题。这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。
这种VR体验通过遮蔽你的视野,使你与周围的物理世界隔离,进入另一个空间——这非常有趣且令人着迷。它也与冥想时的体验相似,当你进入另一种精神状态时。
谢晓泽的“敦煌:重塑藏经洞”项目曾在多个展览场地展出,包括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、上海敦煌当代美术馆、深圳坪山美术馆、伦敦大英图书馆以及北京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等地。